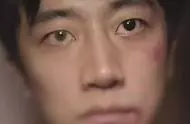 "
"第13屆FIRST青年電影展於7月28日晚在青海大劇院落幕。盛典一號人物胡歌、朱亞文、王傳君擔綱主持人,由謝飛、田壯壯、張家魯、宋佳、曾國祥、鄭大聖、萬瑪才旦、張頌文、姚晨、梁靜、海清、周冬雨、陳柏霖、郭麒麟、鄭人碩等影展嘉賓頒出屬於青年電影人的十項榮譽。
評委會主席刁亦男及評委會成員趙非、述平、陳哲藝、秦昊、查爾斯·吉伯特、查爾斯·德松的爭論終於落定。談及評選標準,刁亦男概括道:「一部優秀電影應該有的傾向是——親近普羅大眾,有通俗化的情懷;導演作為作者,對世界和作者有深切的體驗和感性的表達;同時對電影藝術形式進行徹底的追求。」
那麼以此為目標,具體又要如何做呢?這才是大多數青年電影人的困惑與需要解決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得以在FIRST開設的各種論壇與工坊中被細化、探討,7月25~26日,豆瓣影人PRO在FIRST影展技術工坊與文學改編工坊中一窺究竟。
電影調色如何助力實現敘事功能?
調色能否彌補拍攝中的不足?
中小成本電影如何控制好後期調色成本,如何拍攝出有質感的影片?
電影聲音的構成?
攝影導演工作的本質是什麼?
怎麼定義電影中的文學性?
文學和電影之間各自有對方所渴望的「超能力」?
通過什麼方法來消滅文學和電影的兩種敘事介質的不同?
本次工坊由六位嘉賓——著名攝影師趙非、資深聲音指導富康、畫林映像創始人/首席調色師朴相洙、作家/編劇述平、導演鄭大聖、作家/編劇/導演萬瑪才旦,分別從技術與文學改編兩個領域逐一庖丁解牛,奉上滿滿乾貨。
技術工坊
「光線是立命之本。——趙非
現實主義的戲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錄好同期聲。——富康
調色不是磨皮。——朴相洙
1.關於攝影
代表作:《盜馬賊》《大紅燈籠高高掛》《荊軻刺秦王》《讓子彈飛》
從個人經歷講起
趙非:七幾年那個時候物質水平非常貧乏,我上學之前別說攝影,根本就沒有拍過照片。只是那個時候學過畫畫,比如素描還有色彩,有一些造型意識,之後考試的時候主要也是針對這些基本功。所以我覺得如果希望在攝影師這個職業上有發展的話,這個素質是必不可少的,這對於你色彩的感覺、構圖、運動、調度都非常有幫助。
那個時候看的片子也非常少,一星期看兩部電影,其餘的時間就是就是在學習,看一些書,畫一些畫,看一些展什麼的,我覺得可能是這個到了畢業以後呢,其實還是這樣。
1986年,我跟著田壯壯導演的《盜馬賊》第一次來到西寧,在那個之前,一直也沒機會看什麼片子,到現場有非常多的東西需要處理的時候,其實不知道先做什麼。有人的壓力,有環境的壓力,你會很緊張。我那個時候當然也是慢慢找到拍攝狀態,先從鏡頭怎麼運動怎麼平穩開始,然後再考慮調度的問題。
從這個階段過了以後,我就有機會看一些片了,因為那個時候和義大利領事館有一些文化交流活動,其中《隨波逐流的人》的攝影師,他是我一直最喜歡的一個攝影師,基本上我的很多東西都受他非常大的影響。在《隨波逐流的人》之後我還看了《沙漠天空》,還有《巴黎最後的探戈》,我就覺得這個人拍得特別好,後來從朋友那裡了解到,他也是學繪畫出身的。所以我覺得繪畫特別重要,色彩也非常重要。
最後,光線是立命之本,我在拍攝的每一部電影里都是自己做光線,這個基本功有了之後就可以應付各種情況。包括我到美國去,攝影導演的工作就是布光。
比如《大紅燈籠高高掛》的光線設計,需要有很多技術、技巧。鏡頭裡面人臉和燈籠的光很難協調,如果燈籠用普通的布的話,透光性很差,拍攝的話燈籠是亮的,人臉就會曝光過度。所以當時是找了北影的一個很有辦法的美工師,在燈籠上刷了兌了水的乳膠漆,買了薄的絲綢,就這樣解決了問題。攝影的話要有特別多的招。
《大紅燈籠高高掛》
再比如拍《荊軻刺秦王》的時候,我不太滿足於當時的拍攝方法。升級了,但代價特別高。當時設備不像現在這麼一應俱全,所以在拍攝之前確立了所有的影像風格,包括拍攝方法和具體的燈位圖,反覆推敲過,還自製了很多拍攝設備。
《荊軻刺秦王》
同時我想說,畫分鏡頭和剪輯都是導演一定要做的功課,也是導演的語言。如果導演說我對這個沒有感覺,你有更好的招我就用你的,但在我的理解,這都是導演應該做的事情,要是不做這些事的話,導演就成演員指導了。影像是一個視覺的語言,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導演的工作是在系統很關鍵的環節。
還有一個經驗是,燈不能只擱一個地方,要有很多方案,那個時候跟姜文、小剛、和平這樣的導演合作,他們有時候現場會臨時有很多想法,是要調整的,不能因為布燈影響拍攝。
最後,美工實現不了你的想法的時候,你要及時溝通,讓他明白你的想法,大家一起找解決辦法。
Q:我覺得攝影師和導演有共同風格是非常難的,你在跟導演的溝通過程中有什麼經驗?
趙非:我覺得還是相互感興趣。我有幸跟很多不同風格的導演合作,我很欣賞他們的才華,就儘量配合他們。單純的影像風格特別突出不見得是好電影,相反有很多樸實無華的電影,但導演劇作的力量強大,反而會覺得那個視覺影像風格跟他們的配合特別重要。
我二十多歲時,和田壯壯、張藝謀合作,有時候導演和攝影考慮的問題是不一樣的,有時候是製片方的壓力,希望快點結束拍攝,但出於對影片負責,一定要堅持。他們一定也會理解。
Q: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怎麼拍出有質感的影片?
趙非:資金方面是一個判斷的問題。大家都是從資金很緊的狀況下過來的。有的導演會想這個地方拍點,那個地方拍點,方便剪接。比如你拍了兩千個鏡頭,最後只用了500,如果你提前想清楚,等於資金可以節省了一倍。我們過去有一句話是,到現場拍電影是搞生產,不是搞科研。也就是說到現場不要商量,不能到現場才開始開研討會。
Q:在現場您需要實驗嗎?需要試多長時間?
趙非:我不願意在演員和工作人員都在的時候工作,我希望在他們來之前做完。我會提前去,包括踩景的時候我就會充分考慮。比如《刺秦》裡面,大殿是在河北易縣,後來臨時挪了橫店。我知道是在南方,預計是夏天拍攝,陽光會特別充足,拍出來肯定特別毛,拍出來像新聞似的。後來讓工作人員在屋頂開了個框,不夠亮的時候掀開黑布,亮的時候罩上黑布。
Q:作為攝影師來說,你的工作是服務敘事還是服務風格?
趙非:這個問題同樣困擾我。我一直聽人說,他的電影想要拍成什麼風格,我聽著就很苦惱,後來跳出來,我會想這個景怎樣拍才最好,而不是想具體的風格。我不敢肯定是最好的方式,但我是這樣做的。
Q:我知道您參與了很多不同風格的電影作品,你挑選的時候看重哪些方面?
趙非:早期我看重導演,後來我看重能不能自由地發揮。找志同道合的人很重要。
Q:現在達文西之類的軟體可能可以彌補很多。你怎麼看後期調色?
趙非:你不要上這個當,一定還要在現場儘可能完成。後期調整的越多,質量下降的越多。
2.關於電影聲音
代表作:《闖入者》《南極之戀》《推拿》《風中有朵雨做的雲》《我不是藥神》《地久天長》
a.同期聲
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是年輕的電影人,頭一兩部戲應該都是這種預算相對較少、偏現實主義題材的戲。現實主義的戲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錄好同期聲。
b.ADR(自動對白替換)
《南極之戀》拍攝現場中有很多噪聲,鼓風機的聲音、造雪的噪聲,但是這些聲音都是無法避免的,因為我們要呈現電影最終的一個效果。這種情況下,在電影聲音語言的製作上,我們有一些其他的工藝,以前叫後期配音,現在叫ADR,自動對白替換,演員回到錄音棚去,再現語言的聲音表演。當你遇到有一些特殊的無法避免的聲音進入你的片子的時候,你可以採取這種工藝解決。這部分工作是由純對白部門負責的,他們的工作就是把演員的語言表演錄下來,然後和影像畫面完美得結合在一起。
c.同期聲中的音樂和對白
《推拿》秦昊跳舞片段是同期聲,而不是後期配音,同時記錄了現場音樂和演員對白,相對比較特殊。為什麼說特殊?通常我們有幾種方式,通常要麼是保住音樂,要麼是保住對白。保住對白的情形是不放音樂,或者是把音樂變成頻率非常低的狀況,現場放給大家,我們看到鏡頭中有若干切點,拍戲狀況下我們都知道現場放音的狀況最怕有剪輯點,因為不可能分鏡到每一個節拍的狀況;還有一種方法是我們為了保住表演,我們放音樂給大家聽,後期重新錄製對白。所以其實現場同時記錄聲音和對白,到後期通過畫面剪輯和聲音剪輯共同努力,也是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的。
d.動效(FOLEY)
動效的中文也叫做擬音,是現代錄音工藝的代表之一。在以前電影是沒有聲音的,是《爵士歌王》有了聲音,然後有了同步的錄音,再之後才有了所謂工業化的分工。FOLEY是唯一在聲音部門裡帶有Artist頭銜的,因為這個工種可以幫助演員再現肢體表演,所以他們叫FOLEY ARTIST,只有這麼一個或者兩個人。
e.聲音效果部門
聲音效果部門就是做一些聽起來很貴的事兒,比如像是一些動作戲、警匪追蹤戲,包括一些科幻電影,都跟聲效部門息息相關。當然也不是說現實主義題材就沒有部分。
f.環境效果部門
《清水裡的刀子》這個電影是完全沒有配樂的,也沒有什麼對白。而這段為什麼這麼處理呢,實際上是為了還原西北的地理風貌,有意識地放大了一些在現實環境中的聲音,通過這樣一種小把戲,展現出一種不是很真實的狀況。
g.音樂部門
《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紫金置業發展回溯那段,是典型的音樂主客觀轉換的片段,全是現場收錄的。
h.混錄部門
剛剛聽的都是音樂部門的分層,如果說剛剛以上所有音樂部門都是做一個金字塔式的疊加的加法,越來越高越來越高,混錄部門就要把金字塔倒過來,把最有用的放在最底下,沒有用的留在上面。
聲音能為電影帶來什麼?
a.喚起記憶
聲音能夠喚起記憶,把時間和空間聯繫起來。我們年輕導演在選曲的時候在劇本階段就一定要通過劇作把選曲放到電影橋段裡面,別撲面而來來一首什麼歌,太生硬了。
b.控制情緒
為什麼都說視聽語言?在《推拿》小馬復明時,可以看到在小馬復明之後,我先破壞了小馬的聽覺,讓影像逐步吸引大家,之後用所有聽覺的體驗幫助盲視覺的呈現。視覺聽覺作為感官體驗,對於一部電影來說是相互配合的。
《推拿》小馬復明
3.關於電影後期DI畫面影像製作
代表作:《推拿》《後會無期》《闖入者》《乘風破浪》《流浪地球》《我不是藥神》《繡春刀 II·修羅戰場
Q:為什麼學習調色?
朴相註:調色的好處在於可以看到影片製作的全過程,包括影片如何開展、完成的過程缺失了什麼、試映觀眾有什麼意見,從頭到尾都可以看到。
Q:調色是什麼?調色可以做什麼?
朴相註:調色可以彌補前期的缺憾,前期拍的好,後期就比較放心。我跟別的調色公司或者調色是有點不太一樣,我沒有風格,電影的風格是導演跟攝影師,也就是是主創決定的,我是可以加分的。現場拍的好,我可以做的好,現場拍的不好,我做得不好。如果一個電影,有人告訴我說我調得挺好的,那就是我失敗了,關注不到電影本身的話,我的調色工作根本就是失敗的。
有些電影呢,剛剛說了現場條件不允許,然後通過後期來彌補,我也做過這種事情。但是跟趙非老師說的一樣,彌補不了,只是可以看得比較舒服,根本的問題是沒法改變的。
Q:關於攝影機、鏡頭、攝影技術、燈光的認識
朴相註:燈光、色溫、ISO等等名詞,導演和編劇不太需要知道這些,但是呢,他們得要理解這是幹什麼的,大家要知道這個概念。比如《邊境殺手》這個片子的攝影師,對自然環境的了解程度非常高,日出日落,白天晚上,還是室內室外,不同色溫下的膚色,還有光線的變化,他都非常了解。這個片子只調了5天,因為沒必要,現場控制得非常好,都是按照攝影師的要求,後邊就沒什麼改的。
《邊境殺手》攝影師羅傑·狄更斯
調色不是魔術,也不是磨皮,《小時代》後期是我們調的,人家說哇你們磨皮磨得非常好,但調色不是磨皮。
Q:電影調色如何助力實現敘事功能?
朴相註:作為調色師,要了解電影的需求是什麼,對故事內容本身的理解,對導演意識的理解,以及對目標觀眾的理解。比如在《我不是藥神》中在印度的場景,原本是是比較暗一點的,為什麼後來調得溫暖了一點?因為攝影師回來講,印度那邊很亂,但是相比北京這樣的城市,因為政策等等的原因,病人買不到藥的這種情況,印度反而是很溫暖的。所以我想通過調色表現得比較溫情和溫暖。
而到了《藥神》里徐崢、章宇、王傳君三人出場的畫面,又有點黯淡。其實這個畫面可以加濾色調得特別有范,但為什麼沒有那麼做呢?因為他們三個並不是在做英雄的事,我如果給到很好看的顏色反而是破壞他們要的那種故事。
Q:和大的studio溝通的時候,細節不太好溝通。我會說,畫面看著有點髒,對方就會問,你要什麼數值,我無法回答。
朴相註:這是因為外國人對亞洲人膚色沒有概念。但是這個問題是要問調色師,導演需要明確要什麼感覺。如果還是跟導演要數值的話,換公司吧。
Q:現在觀看媒介特別多,windows偏灰、蘋果的好點、三星的飽和度特別高、華為的更甚,怎麼樣看待對調色的標準?有什麼解決方法?
朴相註:其實已經有解決方案了,但其實無法實現。以前簡單,就是709和P3。現在主要是標準的問題。NETFLIX做了一個標準,但這個標準不是規定。
文學改編工坊
「文學和電影都有著對方極其渴望的超能力。——鄭大聖
如何定義電影中的文學性?
述平:我之前恰好是從事小說寫作的一個作者,機緣巧合又從事了電影編劇這樣一個行業。我覺得在文學和電影的差別上,文學是比較自由、比較隨心所欲的,更多根據你自己的意願,是比較個人化的;電影是群體合作的藝術,在某種程度上,電影是有設計性和目的性的,在一個半小時到兩小時里,你要傳達你的一些東西,是有一些限制在裡面的,小說就好像沒有那麼多限制。
從改編的意義上說,我覺得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是個二度創作,文學它是母體。如果你屬於創作型的導演,像昆汀那種,他不拍電影本身也可以是個作家,作為創作者,他就能更多地能實現他自己創作的初衷。如果僅僅從導演這個這個行當來說,我覺得還不應該有一個文學的基本的東西在,所以我更鼓勵這種二度創作,有一個底子,有一個火苗,有一個文本,在這個基礎之上去改編。
從閱讀上講,從我的個人感受出發,電影在深度上永遠比不上文學,這跟它的屬性有關係。寫作是最簡單的一個事,就是拿一個筆拿個紙就可以做,而電影你得搭景、你得找演員,一堆事兒。我們在閱讀文字的時候我們自動地會有一個想像的空間在,文字提供了一些詞句、段落和故事,你會由此聯繫到自己的一些東西,你會動用你個人的悟性和生活經驗,調動很多自己身上的東西,某種程度上是你在參與這個東西,而且這個範圍很大;反過來電影,它把影像和聲音都給了你,是被動接受,尤其是特彆強勢的電影,基本上你自己思考空間很狹小。
萬瑪才旦:對我來說,文學可以保留很多想像性,每個讀者心中都有一個哈姆雷特。我們看《紅樓夢》的小說,對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物有非常豐富的想像,形象是不確定的,是非常寬闊和豐富的想像,但是87版《紅樓夢》電視劇之後,賈寶玉林黛玉劉姥姥這些形象就留在了你的腦海裡面,限制了你的想像。所以從形象層面講,影像限制了文學的想像。
反過來說,文學也會限制電影的形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獨立的文學作品的形象,很多文學作品改編成電影,原著人物和影視作品人物會有落差,很多人都會對比,比如說《紅樓夢》《白鹿原》中的人物,都會跟電影的人物做一個對比,然後就會有落差,覺得某個人物塑造得不太成功,人物可能跟原小說差別比較大,經常會有這樣的討論。
對我來說,文學改編電影中的文學性更多保留在意象上,文學作品本身有很多的意象,會通過意象傳遞一些東西,如果改編能夠保留這些意象,我覺得是非常好的;第二可能就是一些主題的東西,短篇小說和中篇小說可能相對比較容易,有相對單一的主題,這個主題轉變到影像上就容易保持;第三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對白,有些小說的對話非常精彩、非常具有文學性,全部搬到劇本當中跟演員對台詞的時候,可能就不是特別適合。很多對話在小說中很自然,放到熒幕上就會假,不是說「人話」的感覺。我在把小說對話搬到劇本上的時候,會把自己假設成這個人物來念台詞,或者是在拍攝現場把演員集中在一起,讓他們念對話。
鄭大聖:好像是英國的《視與聽》雜誌,做過一個統計,說全世界的電影各個時期各個階段的電影大約有70%是改編自小說,這個統計包括嚴肅文學,更多的是流行文學、通俗文學,但這個比例竟然有70%。那當然了,從《飄》到《哈利波特》到《指環王》所有這些作品是為什麼出現呢?通過這個事我我一直在想,文學跟電影的關係應該是相愛相殺,海明威否認所有好萊塢對他的改編,為什麼會這樣?我覺得大約是文學和電影都有著對方極其渴望的超能力,比如說我們所有人都認為文學對人的心靈隱秘處的抵達是電影天生難以企及的。
我很願意說的是,電影一切都是關於「像」,因為我們的鏡頭其實只能拍到皮膚,再也拍不進去了。但是反過來,我們有一個一直說的諺語就是「一鏡勝千言」,當視覺的、聽覺的、表演的、情境的整合成一個場景的時候,可能你寫好多張紙,也描摹不了那個瞬間的一個整體呈現。
所以我的感受是,文學和電影它各自有對方所渴望的超能力,這個很可能就是文學和影像一路磕磕絆絆但是也很難離棄然後結盟的原因。行到「字」窮處,坐看「像」起時,文字的盡頭大概是影像的開始,反過來也是一樣,這個當中有各種奧妙無窮的化合反應,從大商業片的導演到作者性的導演,還有直接是作家變導演,我覺得這個特性是不斷吸引他們的原因。
文學作品改編電影取捨
萬瑪才旦:文學作品改編電影首先需要適合改編,比如說我有很多小說,那我會選中適合改編成電影的小說,在改編的過程中,保留了一些東西,然後也取捨了一些東西。
比如《撞死了一隻羊》是兩個短篇小說改編的,那其實小說到電影之間這種改編也很大。《撞死了一隻羊》這個小說,有一段描寫就是他早晨不願意起來,然後他的僱主給他加錢,然後他上路才發生了撞羊的這件事情,但是電影裡面就通過一個場景講述他在高原上孤獨的行走的這樣一個狀態,然後才慢慢把觀眾帶入這樣一個情境。
我覺得那樣的描寫可能是沒必要的,所以就去做了這樣的取捨,所以文學改編,首先我覺得你要看這個小說適不適合改編,拍《撞死了一隻羊》是先看到了次仁羅布的《殺手》,當時就被這個小說吸引,覺得它是一個可以改編的小說,然後因為篇幅再把自己的小說加進來,就這樣一個過程。
文學語言和電影語言的差異
鄭大聖:我改編小說《村戲》是非常偶然的、非常沒有預謀的遇見。小說原作者過世得早,我對這個作家沒有了解。因為不夠了解,我只是直觀地、直覺地就讀到了這個文本,其實真正觸動我變成一部電影的,只是來自於其中的四五行字,而且不是原來那篇短篇小說的主旨,它就是一個動作一個情境,由此展開了此前此後的各種聯想。
我的樸素感受是,文學作品中的很多東西不是那麼容易全面引用和改裝在電影里。小說的作者和電影創作者,他們的關切點往往是不一樣,小說和電影的它的語言也是完全不同的。
好的文學和小說,說到底還是語言好,就是因為它的語言太好了,所以才能夠那麼透徹、那麼準確的達成他寫作上的訴求。電影它沒法直接的借用文學的語言,但是他又渴望能夠完成文學性的意識,尤其是文學性的對於人的心靈、內心和對處境的感知。
這種情況下他要怎麼辦呢?雖然只能拍到皮膚,還是要找一個電影語言能達到的方式,在逼迫之下,高級的電影語言有可能被激發、被觸及,我覺得這個是特別奧秒的。
述平:我們在寫《讓子彈飛》的時候腦子裡突然出現一個意象,就是花姐拿著兩把槍,一手指著張牧之,一手指著湯師爺,我跟我旁邊的人講,他說好牛逼,這是個好的海報。我說不對,我感覺這個裡面有故事,我們去找姜文聊聊。結果一說,姜文就說他感覺感官上受到一種刺激。這是沒有原因沒有結果的,就是受到一種刺激。
就是這個東西是有一些靈感的東西在的,我覺得這個東西某種程度上就是文學意義上的一個東西,並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經過各種推導出來的東西。這個東西可能就是你根據眼前你所提供給你的這個材料,人物關係、人物場景,突然動發出來的一個東西的。
花姐拿著兩把槍,一手指著張牧之,一手指著湯師爺
電影語言究竟是有哪些東西構成的?
鄭大聖:簡單點來說,慣常我們認為一個電影劇本不是獨立的,它是對每一個電影做的一個藍圖的準備。我每次都是跟編劇一起工作,從頭到位我們工作的目標就是用文字這個媒介寫下來這個劇本,想要標示出的是日後這些文字描繪不了的那個東西。
我的一個基本認知就是文字結束的地方是影像開始的地方,所以我儘量想把劇本準備到作為文字的備忘計劃,作為一個藍圖準備。
我還想補充講一直以來我私下裡的一個期待,就是我多麼想看到一種文體就叫電影劇本,而這個劇本不是為了拍攝,就像我們看過很多裝置藝術家的概念圖,我們看過很多建築師的概念圖。最早我這個啟發是來自於讀到吳念真或者朱天文前輩的電影劇本的時候,我發現不管侯導最後拍出來的那個電影是什麼樣,我只看他的劇本的時候,我相信是電影劇本是有它的文學性的。它的節奏不一定是小說式的節奏,但是裡頭竟然有電影感的情境,包括剪接點都有,就是那種節拍。
我們講中國人的那個史書,完全是劇本,就是我們的史書的傳統是述而不作,你完全可以看它的時間、地點、場景、人物,沒有內心描寫。所以這是我自己的一個暗暗的期待。
END.
"
文章來源: https://www.twgreatdaily.com/cat123/node2142954轉載請註明來源:今天頭條
